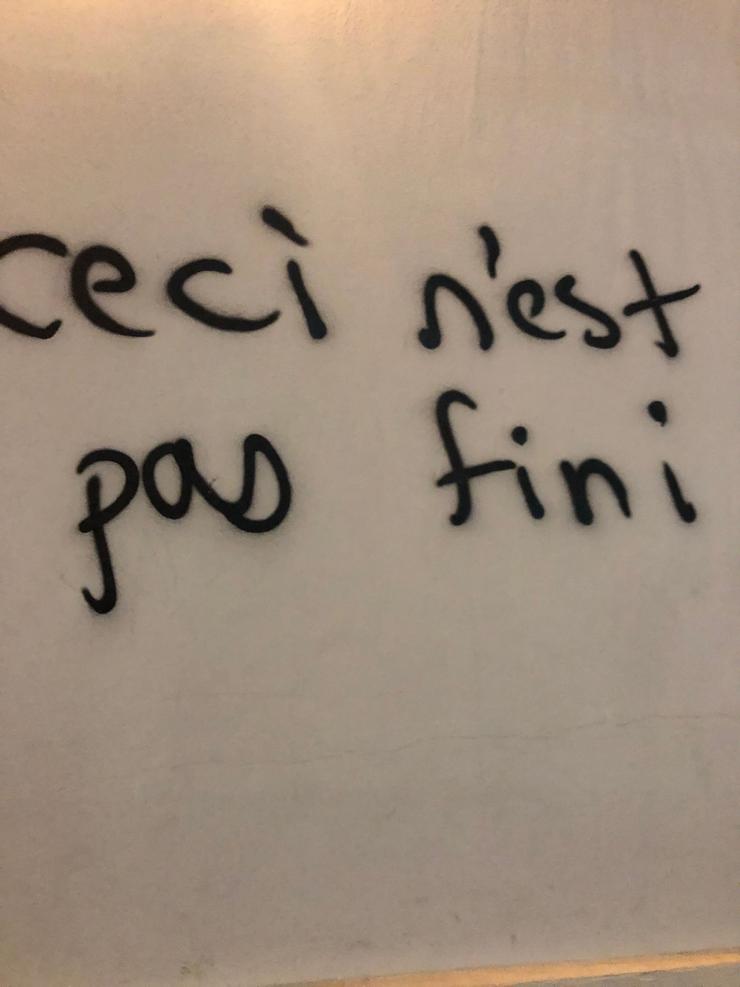讀短篇,我喜歡寫短篇。
短篇
之前經常會想,我寫這樣的文字有保存下來的必要嗎?
對我或對別人又有什麼意義?
也經常不確定自己為什麼讀那一個個的故事,畢竟也不會說給別人聽,可是說起來,我不是一個太務實的人,沒必要就算了——既然做的許多事都沒有意義。
我只是想在有空的時候翻著幾頁⋯⋯
躺在床上,任由歌單自主播放。
那是《Paris early morning》的歌單,這標題應該要讓人打起精神的,卻越聽越睏⋯⋯一邊讀著契訶夫的短篇,很幽默很有趣,可是讀著讀著睡著了。想像的是他那帥氣又一臉不屑的臉,冷冷的敘說著這些諷刺的故事。
看了時鐘,大概昏睡五分鐘,此時正播到法國歌手Camille 的〈La jeune fille aux cheveux blancs〉,我被那個低鳴的頻率震醒,背景音又是尖銳的女聲合音,醒來後馬上又想睡,好像小學夏天在悶熱的教室聽著老師平淡的口吻,經常不小心睡著幾分鐘,醒來那瞬間精神飽滿——大概是被嚇醒且感到羞愧——之後聽著電風扇的轉動聲,再次不小心睡著,頭越來越沉。
不記得課堂上聽了什麼,也不記得短篇故事說了什麼。
瑪黑區的女孩
她曾住在瑪黑區一個猶太人的公寓閣樓,老太太租給她的。
前一年她大學落榜就決定到巴黎去學戲劇,那時還在語言學校學法文,此前一點基礎也沒有,甚至連英文程度都不太好,自然是很難與人溝通。
但她聽懂了。
老太太說,洗完澡請把所有黑色頭髮清乾淨,「我不要在浴室看到一根黑髮,那很噁心!」我直覺的問:「那家猶太人沒有黑髮的嗎?」
當時女孩已不是女孩,是中年女人,她說:「孩子,那是種族歧視,你聽不出來嗎?」我只是想幽默但沒有掌握好。
後來她和老太太讀醫學院的孫子談戀愛,把老太太氣得半死,我不確定那是不是出於一種報復,還是他們真的相愛了。「然後呢?」
她說,畢竟自己連大學生都不是,自認也不可能真的被猶太醫學生接受,認為對方只對她感到好奇才交往,不會長久。
法文學好後她去比利時學戲劇,兩人再也沒相見。
猶太學生只是人生中的一個插曲,但她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一個有結局的故事,年輕時的我覺得好悲哀。
聽著故事心裡想,也許以後回憶起巴黎的事件也能輕輕敘述,在許多年後終究只是個背景。
時間
最後一次和巴黎男見面,包裡放了一本尼采的時間觀。他忙著用電腦工作,我把書拿出來消耗。
無聊了,問我在看什麼書。那是一本中文書,但封面用德文寫著「時間」,他看了一眼又繼續工作,幾分鐘又問「那是『荷蘭文』嗎?」
他知道那是德文字,卻把「德文」說成「荷蘭文」。
幾個月後,我們在WhatsApp上聊了尼采的時間觀,我只是賣弄那本書上讀到的,而他剛好本來就很喜歡尼采,一定知道我不精。基於禮貌,沒有戳破我可能的瞎扯,以前他常說,「我不喜歡你騙人」即使我只是將照片修得好看一點。
那時我明白了自己的道德觀已不歸他管。
依然記得這些無聊的細節,但早不記得書中寫了什麼。